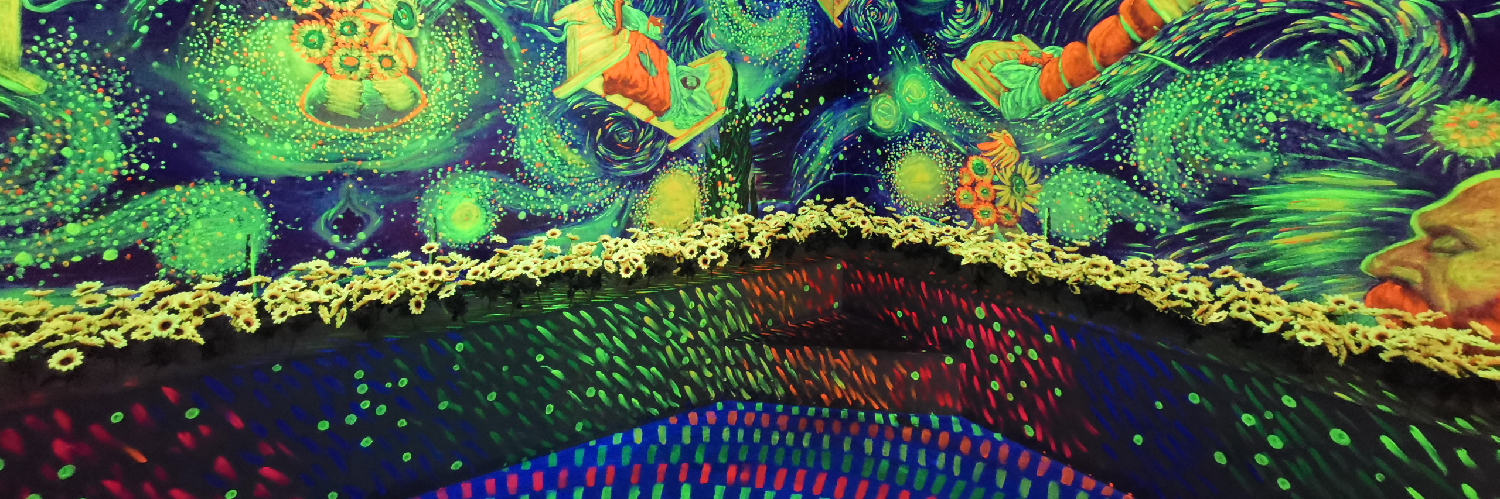
wecrashed
简介:美剧,AppleTV出品,同名播客改编,真实事件,共八集
4.19:目前看到第七集,处于雪山崩塌的前夜,按照现实时间看应该是2019年左右,一级市场融资推向顶峰后,所有人(投行、VC、公司)都等待一场四百多亿估值的IPO兑现所有人的成功,而事实我们知道,这是一场对局外人意料之中的失败,最终IPO破发,市值仅到百亿左右,无数员工挥霍一把后发现期权无法兑现,而始作俑者adam两年后仍然能够得到几十亿美元的遣散费,不算耻辱地离场。
感想
最开始看这个剧,因为自我进化论主播Athena的推荐,她是一个倡导灵性和禅修的博主,她从里面看到了很多创业和灵性相关的东西。在最终决定看这部剧之前,我去豆瓣看了一下评分,只有7.6分,对于这个配置的美剧来说有点过于低了,直到现在我也不是很理解,只能姑且认为是大众对于故事本身的不满意,将真实故事背景下的愤怒迁怒于影视作品。对于我自己来说,至少它是一部可以下咽的剧,在我的审美里,不比前几天看的漫威快餐剧月光骑士差。
很多人认为这里面的adam在模仿乔布斯,或者说AppleTV出品的剧,有意识地在将Adam这个角色向乔帮主的角度塑造,我其实不这么想,我甚至认为做出这个评价的人过于傲慢了,就像那些不了解灵性或者禅修的人,不仅认识不到自己的无知,还要用一副局外人看封建迷信的高高在上的态度做出一些片面的评价。
这是一种很常见的心理防御机制,当人面对陌生的事物和环境的时候,处于恐惧的心理,会做出一些很绝对化、偏执的负面的评价,我在Steve说的播客中了解到这个现象,深以为然,同时在自己的人生经历中得到了印证
这种恐惧,最大的害处在于无法让人充分地活在当下,永远处在不满现在,怀念过去的状态
说回这个剧,我不认为Adam的充分的灵性践行者,从商业的角度看,他是一个误入科技圈的天才销售员,我们认为的wework的失败,是站在科技投资角度做出的判断,如果Adam当时加入的是传统的房地产领域,未尝不是一个成功人士,当然一个普通的千万富翁,不如一个创造了巨亏投资的科技圈人士来得出名。
从灵性的角度看,这是一个误用了自己天命的人物,他其实没有得到过多少灵性指引,他最大的导师是他的妻子R,R虽然是一个辅修了佛学的富家小姐,但她自己都还没活明白,甚至连开悟都离得很远。R在做瑜伽老师的时候,就可以因为Adam一次拯救,而献身于她。后来wework如日中天的时候,她一下子觉得自己没有价值了,为了证明自己的价值,做出了很多疯狂不可理喻的行为,要求camp的时候全公司吃素、开掉自己的闺蜜取而代之、因为很多无厘头的小事开除员工、在没有充分规划的情况下就创办了一所学校。
我也不知道真正的灵性创业是什么样子,只能用其他的创业者进行比较。我们比较熟悉的创业者是乔布斯,至少他是一个成功的商业人士,他的坚持和独裁是用在自己的产品追求上,而不是用在无止境的扩张和并购上。而另一个灵性大师迈克尔辛格更加不同于Adam夫妇,能写出臣服实验的人,必然不会让自己的喜好影响到个人决策乃至全公司的命运。至少这两位都知道自己的天命是什么,在工作的时候有着无比惊人的热情,同时没有强加自己的爱好于其他人。
我其实很反感素食狂热,首先,基于修行目的的吃素和基于环保怜惜动物的目标吃素是不同的,其次,即便是基于修行目的的素食,也是顺其自然的,就像我昨天听的晚风说那期,当自己修行到某个境界的时候,身体会发生一些改变,呼吸会变得更加深长,只能到肺延展到脚部,而开始选择吃素只是身体的另一种自然选择。最后,吃素不是强迫行为,不应该为了某种主义强迫自己,更不能强迫其他人。R这种行为之伪善,在我看来和梁武帝又有什么差别。
Adam作为一个口号上的灵性创业者,在他的成功经历中,离不开大环境的影响,从命理学的角度看,他利用了命和运之上的势,也就是时势(风口、周期),他的创业是在uber和Airbnb普及了共享经济之后的时代,又是在这两个龙头企业还没有IPO上市破发之前的好时机,免去了一级市场的教育成本。他口号的灵性主义让硅谷一些同道中人满意,同时他也利用了孙正义某些方面的人性弱点,占尽了天时地利人和。但一切终究是动态平衡的,wework落到最终的结局是最好的平衡结果。
存在主义咖啡馆
(看了一点点)
主线:海德格尔和萨特,穿插其他相关人物——胡赛尔、波伏娃、加缪、梅洛庞蒂
分别代表现象学+存在主义
标题含义:想象在一个法国咖啡馆里,某个时刻,栖居了上面所有的人物
19世纪先驱:北欧的哲学家?、尼采
都是对传统哲学的反叛
前者在生活力图在方方面面改变人的预期,让人去面对那些没有预料到的情况
尼采:上帝已死?
现象学:从生活现象中发现哲学,例如从研究面前的煤油灯了解哲学。吸引了萨特20世纪30年代想去德国学习
40年代,存在主义以一种亚文化的方式出名,摆脱传统的中产阶级生活方式是年轻人的追求——熬夜、和不同种族的人交往、不在乎等级和身份地位。但只有萨特和波伏娃认领了存在主义
存在主义:人区分为自由的和不自由的,在混乱和不确定的世界里,我们是有选择的,选择的自由使我们不断成为自己,人和其他的事物的不同在于人无时无刻都是变化的,等同于笛卡尔我思故我在的反面,我们的存在先于经验和思考(本质)
栖居哲学:哲学不仅仅是一份职业,而是整个人生都放置在哲学中,存在主义哲学家通过不断的人生选择,来支配自己的人生,比如萨特和波伏娃的关系,选择不尊崇传统的婚姻关系(因为意味着会放弃很多想要的东西,在其他方面不自由)、萨特拒绝法兰西院士、诺贝尔文学奖,坚持体制外的生活,将自己的思想观点排除在关联利益之外
存在主义在80年代被结构主义认为过时,但到现在很多当年的社会议题仍然没有解决,人们又开始讨论起了自由的问题,把视角重新转移到存在主义上
《成为波伏娃》笔记搬运
作息
波伏娃和萨特在很年轻的时候,就有一种信念,认为自己有天命在身,写作的天命,哲学的天命。在人生很早的时期,就深感自己与众不凡,未来会有所成就。
波伏娃十几岁的时候就苦读哲学,制定了非常严苛的作息表,要求自己每天高强度的阅读和写作,假期制定好大大小小的规划,要求自己啃下各种哲学大师的著作,同时有规划地学习英语和法语。对于规划她基本都坚持并实现了,她很早就能直接阅读英语和德语原文的书籍(文学和哲学),相反萨特不行,在英国访问期间,波伏娃想去看狄更斯相关的文化古迹,而萨特兴致缺缺,更想去深入探访英国底层工人
萨特和波伏娃的性格差异
波伏娃有非常“女性”特质的情感,这是很多人在评价波伏娃,用一个女性主义视角下的判断,仿佛为了证明这个写下《第二性》的作者在感情上是多么的自相矛盾,多年来,不断有文学评论和艺术圈内人士试图通过自己的二次加工出另外一个感情善妒的波伏娃形象,向当时的公众和后代传达出这个名女人的可怜和可恨之处
在我看来,这种拙劣的明褒暗贬手法过于低级,实际上波伏娃在和萨特的工作和友情中,有非常多的理性的一面,如果用传统的话语表达,她非常的男性。在早年的信件中,波伏娃常常苦恼于她所爱的男人还有其他的爱情关系,她会妒忌和害怕,同时也会为了爱人的离别而心酸,而萨特往往会鄙夷这种人的情绪化,相信人应该用理性生活,但仅仅从这些片段,我们不能武断地认为萨特比波伏娃更加理性。
从生活规划上看,波伏娃显然比萨特更善于做精细规划,她的外语掌握得更好,外语首先需要大量时间的投入,这涉及到了生活的高度计划性。其次,研究表明,影响逻辑能力和外语能力的都是人类的左脑,而且她的阅读量更加宽泛,她比萨特更加重视阅读量的积累,看重从他人之处得来的智慧。还有一个关于她善于时间规划的佐证是,她一次性通过了国家哲学教师考试,和萨特不分伯仲,有传言萨特能拿第一名仅仅因为占了巴黎高师的出身优势,阅卷人觉得巴黎高师比索邦更适合拿到第一,而这是萨特的二战考试。
而相反,萨特一定就不情绪化吗?我看未必,人通常挂在嘴边的都是自己缺乏的,当一个人过分强调理性,那他可能就是非理性的。萨特花花公子的属性来自于他对自己长相和身高的深度不自信,这种不自信本身也是非理性的。他在很早的时候就开始尝试精神药物,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持续了甲虫幻象,本质上是出于深度的空虚和不安。如果按照神秘学里面关于能量的说法,双方都有信念,信念是双方的能量来源,而波伏娃总体能量是高于萨特的。
电影 《花神咖啡馆的情人们》
能看完,但中间分心玩手机多次。看过了传记再来看电影,就仿佛在考证。
很多人批判这部电影将波伏娃在关系中的地位处理得过于低下,诚然我部分认同,电影中波伏娃在关系初期一些姿态太传统女人,当萨特在她的女学生处受挫时,他回到房间打碎了镜子,波伏娃第一反应是像一个母亲一样把他拉到卫生间,一边帮他处理伤口,一边安慰他自己再帮他介绍一个漂亮的斯拉夫女学生。在她一次重度肺病独自卧病在床时,她的母亲前来看望,问她萨特呢,为什么不来照顾她,她却愤怒地解释她和萨特是特殊的关系,所以萨特不用来照顾她。这两端对比起来,不禁让人觉得波伏娃连中国封建大家庭的大婆还不如。在一段关系中,只有义务没有权利,因为看过传记,我知道这不是真实的波伏娃,但是导演和主创团队作为法国人,认为这是他们眼中的波伏娃,他们为什么会这么想和这么做,这背后的问题更值得我们深思。
波伏娃后于萨特成名,有此消彼长的关系
40年代陆续有作品出版,但还没有成为著名作家,此时萨特已经出名,合办《摩登时代》
50年代有自传性质的小说拿了龚古尔奖,出版的《第二性》销量特别好,在多个国家引发轰动,虽然英语的翻译很糟糕+有诸多删改,直到21世纪才重新翻译出版了英文版本。此时波伏娃日渐在国际女权运动中占据重要位置,而萨特因其政治观点冷门,逐渐边缘化,同时遭受严重的情绪问题,药物依赖严重。
变老的恐惧
进入到五十岁,开始忧虑变老的问题,年轻16岁的情人也在某一年终于结束了爱情关系,退化到友谊,后来又有新的青年学生和波伏娃建立了关系。母亲罹患癌症,在她去世前六周,波伏娃一直陪伴在病榻,母女关系缓和了很多,她把诸多感悟写到了作品里。
写作是她对抗衰老和死亡的方式,母亲和萨特死亡的时候她通过写作和出版缓解自己的情绪。
70年代第一本关于老去的著作评价不高,和她的写作方式有一定的关系,认为写得过于笼统和难懂。她研究了大量先贤和作家对死亡的描述,写成了第一部分的综述,然后开始在第二部分写自己的看法。
她的一个重要观点是老去最可怕的是孤独。她认为自己的人生大部分时间是不孤独的,有最亲密的朋友们的陪伴(扎扎、萨特、各种男性情人、西尔维),但随着年龄增大,特别是萨特死后,她的孤独感日益增重。
政治观点
主张是社会主义和左派的,1955年在中国访问一个月,产生的灵感后来写作了《长征》,支持阿尔及利亚的独立运动,反对法国政府,和萨特分别收到过死亡威胁
女性主义,公开谈性和女性的自由,第二性出版后每天花1小时和读者通信,鼓励女读者追求自我
巴以冲突支持以色列
60年代开始写自己的自传,得到的关注很高,但也将她和萨特的关系公之于众,让萨特的一些情人不满。她一直在反思她和萨特的关系伤害了一些第三人
萨特的离世
萨特死前有很长一段身体衰弱期间,波伏娃承担了照顾陪伴健康和全力承担编辑工作的责任。萨特死去后的那个夜晚,她曾经爬上病床和他待了一段时间。
之后萨特的讣告中只有一部分提到了波伏娃,他的所有相关遗产都是阿莱特处理的,波伏娃要求拿到萨特一本著作的手稿,但是没有得到同意。之后波伏娃出版了萨特和她的通信,声称是萨特生前的要求,她一直信奉的是伏尔泰的名言,给生人尊重,给死人真相,但这也直接到了她和奥尔加姐妹关系的破裂。
在萨特死后,她收养了西尔维,因为她的妹妹不在巴黎,没有办法从医学和法律关系上担任监护责任。西尔维一开始很反对,因为西尔维目睹并厌恶阿莱特在萨特事务上的处理方式,但最后还是同意了,西尔维有正式工作——作为一个全职的哲学教师。
在她去世前的几年,仍然在写作和积极参加政治上的女权运动,这个时候法国有了女性的政党,更激进的女权宣言,但波伏娃并不认同,认为是一种暴政。
这些年,波伏娃仍然对身边的亲朋很慷慨,在她的坚持资助下,朗兹曼的影片最终上映,并在上映前由波伏娃公开写了赞扬的文章(发表在上映前,是因为担心无法活到上映时),同时还资助了妹妹在斯坦福大学举办画展。
死后
很遗憾的是,波伏娃死后的讣告,大部分都提到了萨特,更讽刺的是用和萨特的关系来贬低波伏娃的成就,认为第二性是在实践萨特的哲学,她是萨特的一个好学生,还有一部分讣告直接贬低波伏娃的文学和哲学成就。其实在生前,波伏娃的男性朋友确实一直有对她的作品提出尖锐的批评,认为要不是过分难懂,就是不重要。
按照波伏娃的要求,死后她和萨特通信中她的部分被出版了,这个时候受伤的是另一个生者——比安卡。
女性主义支持者和女权运动,对她褒贬不一,反对者两种观点,要么认为她过于女权,要么认为她不够女权
日本
波伏娃六十年代和萨特到访日本,因为第二性的日文版本出版,她在日本受到了热烈的欢迎,访日期间做了一些公共演讲,给日本女性提出了一些建议,比如要争取经济独立。
诚然,波伏娃在后进的资本主义国家受到热烈的欢迎,甚至欢迎更甚于老牌的资本主义国家比如英美,她的晚年,她的名气在美国依然很大。也让人思考,为什么从政治上看全世界的女权运动都有了巨大的进步,但是从经济社会文化上看无论是哪个国家女权仍然感觉有种在封闭的环境中做布朗运动的趋势。
在老旧的波伏娃纪录片中,有一段材料说的是dupont夫人的婚后生活,虚构的是一个几千万法国妇女的缩影,一个女人在婚后如何丧失了作为人的自由,一旦结婚,就有不低的概率需要面对丈夫的出轨、不忠和欺骗,经历作为人的财产权和政治权利的丧失,浪费大量的时间在处理家庭事物、等待丈夫和保持美丽上面,现在的社会又好在哪里,全世界的中产阶级幸福生活的幻象依然没有改变,在美国英国法国日本仍然一样,在第三世界国家贫穷的女性受到了更加严重的剥削,在更低的生活水平下需要养育更多的子女,还要出门打零工补贴家用,甚至在一些国家家庭中的女性需要出卖自己的身体卖淫或者贩卖器官来为家庭贡献更多的价值。
波伏娃首次到访中国的时间是1955年,比访问日本的时间提前了十年以上。当时的中国在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实践,所做的实验不仅仅是经济和政治的,还包括婚姻文化和家庭生活,通过集体化来破裂坚固的宗族社会,同时也冲刷了原子化的小家庭。在这个时期到访中国,波伏娃受到的冲击是剧烈的,作为一个算得上激进的左派,她对当时的中国社会怀有的情感是正面和强烈的,使得她回法国以此为题材写出了《长征》。
放在2022年的中国,读到这段往事百感交集。当前的微博热搜是,一个有点小权力的地方体制内精英,在家庭中疯狂殴打他的妻子,因为监控视频的流出,其残暴和不人性令公众哗然。在一个女性声音居多的社群里,女性忧心的话题是,在受到家暴之后,如何能够顺利的离婚,从中走出来(家暴仍然不是法定离婚的理由之一,同时目前还有离婚冷静期)。
这一两年,波伏娃的著作在中国重新走向了流行,80年前的运动思想的先驱放到现在仍然不过时,于波伏娃既是夸奖,又是讽刺,更是时代和社会的悲哀。
- 空
- 一切法皆是佛法
- 适度
- 长的不放时间轴
- 什么都看
- 不排斥神棍,but no New Age
随便记记
